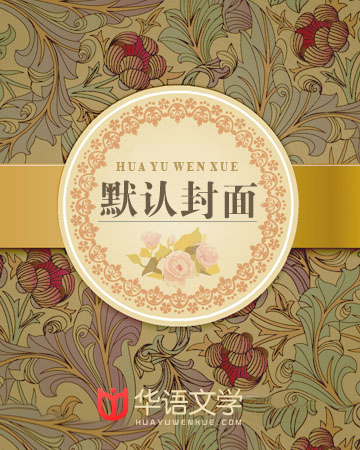老木资深作家
暂无
还没有填写个性签名
-
如今诗歌在中国,正处在一个艰难跋涉的时期。一方面,诗作为文学表达形式中最形而上的方式,其先前静思、独吟、反复推敲……的生成环境已经与当下的市场规律发生了严重不适应的情况。商品交换的残酷竞争和快速周转的急迫,压缩了诗歌的环境。人类生存为先的生命原则,迫使人们不得不首先把注意力放在谋生的“钱”上。因此,诗歌被迫进入了又一轮衰颓,似乎成了“有闲人” 的 “病号饭”。经济的爆发和旧式道德的溃退,物质的增长与过去文化的衰落都是必然要发生的,世界和中国现阶段发展的现实和现状也是必然不可更改的。文化正在波浪式运动发展的低谷期。另一方面,中国现阶段的文化格局,仍然停留在清末西方凭借坚船厉炮带来的西方文化被片面独尊的状态。它像强龙,与被压抑着的,依赖固有的语言、地域和习惯的基础,不甘泯灭、拼命挣扎的东方文化相互矛盾。这使得东方,尤其当代中国的主流思维标准和尺度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混乱——既“抛弃、背离了固有的传统”,又没有“全盘西化”成“现代普世价值观”,也没有形成新的、符合当前社会发展现实的独立价值体系。因此,在东西方文化二合一整合未果的情况下,许多社会思潮互动交错,让人们无所适从。表现在诗歌上,有的倾向于复古,有的走向纯抽象、纯荒诞,有的则走向打油、回车。使得诗歌整体的规模、影响力和动能小了,却出现了繁荣的多样化局面。有人惊呼诗歌不再了(如韩寒),有人则把诗歌奉若神灵;有人复古地崇尚格律、否定诗歌的其它形式,有人则崇尚自由,对“打油诗”、“回车诗”、“梨花诗”……情有独钟。其实只要认清诗歌的性质和意义,诗歌的多种倾向就都能接受。诗歌不过是人们对生命与环境(这里指大环境概念)相互作用关系的体验及表达的一种形式。不同的诗歌只是不同作者的思想表达形式或者叫做表达方式不同。
更新时间:2015-12-16
-
喜欢摆弄文字的人都喜欢给自己起个笔名。起笔名这事有点像给自家的小孩子起名一样,本来很简单的事,却常常越琢磨越费思量。因为它除了符号的作用以外,还要尽量与主人的气质、形象、喜好等相近。再讲究一些,还要考虑生辰八字、卦象、数术,读音、字形,组合、偏旁等诸多讲说。十几年前,在捷克第二次办报纸时候,常写一些有针对性的时事评论文章。为了避免与被评者直接发生冲突,便有了起笔名的需要。作为全业余写手,老木自然不敢有那么多讲究。起笔名的标准自定为简单、质朴、淡然。结果选来选去,发现自己名字的第一和最后两个偏旁:木、十既可理解成名字的缩写又符合自己的直觉喜好,与本人属木的命格也相合,好懂易认,书写简要、读来上口,没有繁简之别,毫不张扬,朴素别致。将二字竖排,便是“本”字。恰合老木悟善归道、天人合一的座右铭——道者,万物之本。若附会强解,亦可巧思臆想,生发出一些所谓“时尚之说”: 木者,人 + 十,俨然耶稣背着的十字架、人神合一的样子。他是被老爸派来用自己的生命来救赎人类的。他没有带来阿里巴巴的咒语、没有带来金鱼给渔婆的如意盆、也没有带来什么“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的治世良策。他只是用自己的生命把人们欠他老爸的帐“顶”下来,“无息借贷”给万民百姓,允许人们自觉地一点一点地按揭还给他。这么烦琐又充满风险的顶帐与按揭,在今人看来,必定是拿了老爹的巨大 “回扣”。所谓“无利不起早”嘛! 木本来是圆形的,又有圆滑、通融之意——也就是说有灵活变通之能。明明说了“不”的事,它偏偏要设法超过一点点——尽管只是一点点。像我们国家法律的实施、像我们目前正努力惩治腐败,总是可以通融一点点。也像我们现实中的感情和婚姻,在笃信和怀疑之间,有人说“不”,也有人说“木”。对,只出差一点点。“木”看上去有点傻傻的,很中庸的样子。其实是装傻、藏拙。而装傻是国人最有效、最拿手的利器。 木又有一种坦然和淡然的气质。你看那路旁的老树,似乎憨臬臬地伫立了几百年、上千年,谁都没在意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它静静地观察身边发生的一切,为而不争、观而不言,临风雪而不避。它淡然自在,从来不想展示什么,也不必说给世人什么。春属木,因而木还有生发之意,它努力进取而不属于灿烂辉煌,独处,它冠盖留荫、造福人间;群聚,则携手成林、共担风雨。还有朋友调侃说,木十乃木石谐音,暗含“木石前盟”比喻,昭示动人而枉然的悲剧爱情……随着年龄的增长,朋友们给木十名字前冠以“老”字,以为敬称。不多时,大家嫌麻烦,省略了“十”字,简称老木。于是便有了后来的“老木”这个变化后的笔名。好想真的像一株入世而不争的老树,默默地站在一隅把自己的观察、思考、感悟用文字记录下来,捡有用些的留给后人。本书的散文,就是在这种心态下、在十几年的时间里逐渐写成的。散文是我从事文学写作后首先发表在捷克报纸以外刊物的文体。由世界华文作家协会的付兆祥秘书长和欧洲华文作家协会的莫索尔前会长推荐,经台湾《中国时报》方梓编辑的辛勤组稿,发表了散文《石子路》。随后应方梓之约又发表了两篇。从此打开了我“门外”的文学写作之路。所以,在本书付梓之时,我诚以感恩、感谢之心,向付兆祥、莫索尔两位老大哥和方梓女士致以深深地感谢,并以挚爱之心感谢家人多年来对我的支持、理解和爱护。其实我的第一篇散文是收入本书而从未发表过的《端砚》。是一九九四年父亲去世后写来纪念父亲的。我愿意就本书的出版,向我书中多次提及的已经过世的双亲致以深深的追念。相信他们的在天之灵一定会向他们一直引为骄傲的儿子投以满意的微笑的。
更新时间:2015-12-16
-
更新时间:2015-12-21
-
更新时间:2015-12-21